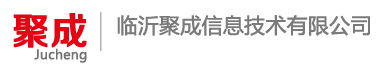很慶幸,隨著市場的不斷成熟,“公關(guān)”這個職業(yè)在一二線城市逐漸被“洗白”,陪酒吃飯的淺層認(rèn)知已經(jīng)慢慢成為過往。同時,對于這個職業(yè)中各個職位也有了一些認(rèn)識,例如“ 媒介”這個職位。
大部分公關(guān)認(rèn)為, 公關(guān)公司的媒介=發(fā)稿機(jī)器。大部分媒體認(rèn)為,公關(guān)公司的媒介=軟文輸出機(jī)器。
這種認(rèn)識,3年前的確沒錯,甚至不少媒介自身也把自己定位于發(fā)稿。于是,媒介逐漸成為公關(guān)體系內(nèi)的一個尷尬角色。因為在當(dāng)時來看,除了發(fā)稿和找人幫忙發(fā)稿之外,似乎找不出媒介的更多技能。但是,稿件落地又必須由媒介來執(zhí)行。
或許就是在這種狀態(tài)下,不少媒介都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(huán),就是沉寂在發(fā)稿和尋找人幫忙發(fā)稿這兩個狀態(tài)中,同時,業(yè)界對于媒介價值的衡量也一度從成本控制和發(fā)稿范圍這兩個維度作為核心來進(jìn)行考核,大致概括就是,只要能發(fā)稿,又能找到人(媒體)幫你發(fā)稿,你就是個好媒介。
終于,在這種畸形的模式下,媒介,作為公關(guān)這個“智業(yè)”中的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,卻成為缺乏思考的一個職位。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,我的很多從事媒介工作的朋友都在從業(yè)幾年之后紛紛開始轉(zhuǎn)行,認(rèn)為媒介缺乏價值和競爭力。
尤其這兩年,在傳統(tǒng)平面媒體和 網(wǎng)站受到社會化媒體的強(qiáng)烈沖擊之后,一夜之間,過去的種種發(fā)稿方式都行不通了,同時,客戶對于媒體的選擇也越來越嚴(yán)苛,而媒體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。于是媒介的壓力變得更大。所謂的職業(yè)價值和競爭力似乎也隨著傳統(tǒng)媒體的沒落而日益消逝。
更加可怕的是,隨著“公關(guān)”不再是吃飯陪酒的代言,客戶自身的公關(guān)能力也在不斷加強(qiáng)。無數(shù)媒體人搖身一變成為你的客戶,但從發(fā)稿的角度來看,似乎他們比你更有優(yōu)勢。同時,企業(yè)也逐漸告別過去“一遇媒體變鴕鳥”的模式,更多的同媒體建立合作。媒介的作用又一次被削弱了。
在這“內(nèi)憂外患”的狀態(tài)下,愿意在公關(guān)公司做媒介的人逐漸減少,媒介這個職位也變得更加缺乏吸引力。
但是事實(shí)卻不是這樣的。
其實(shí)在目前看似暗淡的狀況下,對于媒介來說也同樣擁有巨大的機(jī)會。
如今,傳統(tǒng)媒體都在轉(zhuǎn)型自救,我們可以看到較早的時候,人民日報帶頭玩起了官微,擁抱社會化媒體;我們也可以看到,新華社以及其兄弟單位,組團(tuán)構(gòu)建新聞類APP;我們還能看到,東方早報集團(tuán)制作了界面和澎湃兩個風(fēng)格迥異的新聞平臺。
同時,有一個曾經(jīng)的電視人,通過社會化媒體和移動互聯(lián)網(wǎng),打造了一個叫做“邏輯思維”的自媒體平臺。還有一個曾經(jīng)的財經(jīng)作家,利用微信這個產(chǎn)品,建立了一個叫做“吳曉波頻道”的個人平臺。
還有幾位傳統(tǒng)媒體人,打破體制的“禁錮”,建立了在業(yè)內(nèi)極具影響網(wǎng)站,他們叫做“虎嗅網(wǎng)”;“鈦媒體”;“好奇心日報”。
對了,還有幾個曾經(jīng)與媒體沒有絲毫交集的人,他們深度利用了微博,通過一類叫做“段子手”的人群,打造了三個以微博為載體的媒體集團(tuán)。他們叫白耳,售樓,還有銅雀。
寫到這里,突然想起了羅素的一句話:合理地追求個人幸福一旦成為普遍行為,就足以再造世界。
媒體的變化,除了技術(shù)原因之外,或許就是一個個媒體人在追求個人“幸福”的同時逐漸產(chǎn)生的。
那么媒介的機(jī)會在哪里?
其實(shí)就在這些變化的背后。
媒介完成工作的同時,無形中成為媒體人之外,對媒體最了解的人。至少從公關(guān)層面來說,媒介無疑是最了解媒體的。甚至部分媒介對于一個媒體的了解會超過在這個媒體工作的人,畢竟旁觀者清。
那么,在媒體變化的過程中,按照常理來說,媒介對于媒體的變化應(yīng)該是最敏銳的,同樣,在變化之后,如何與媒體進(jìn)行合作實(shí)現(xiàn)雙贏也是媒介應(yīng)該去思考的。
總結(jié)來說,現(xiàn)在的媒介在發(fā)稿之外,還應(yīng)該對于不斷變化的媒體環(huán)境進(jìn)行思考,憑借對媒體的認(rèn)識,對媒體的發(fā)展進(jìn)行有效判斷,更重要的是勇于對新的模式進(jìn)行探索和嘗試。畢竟,看到螃蟹之后,還是要做第一個吃它的人。
|